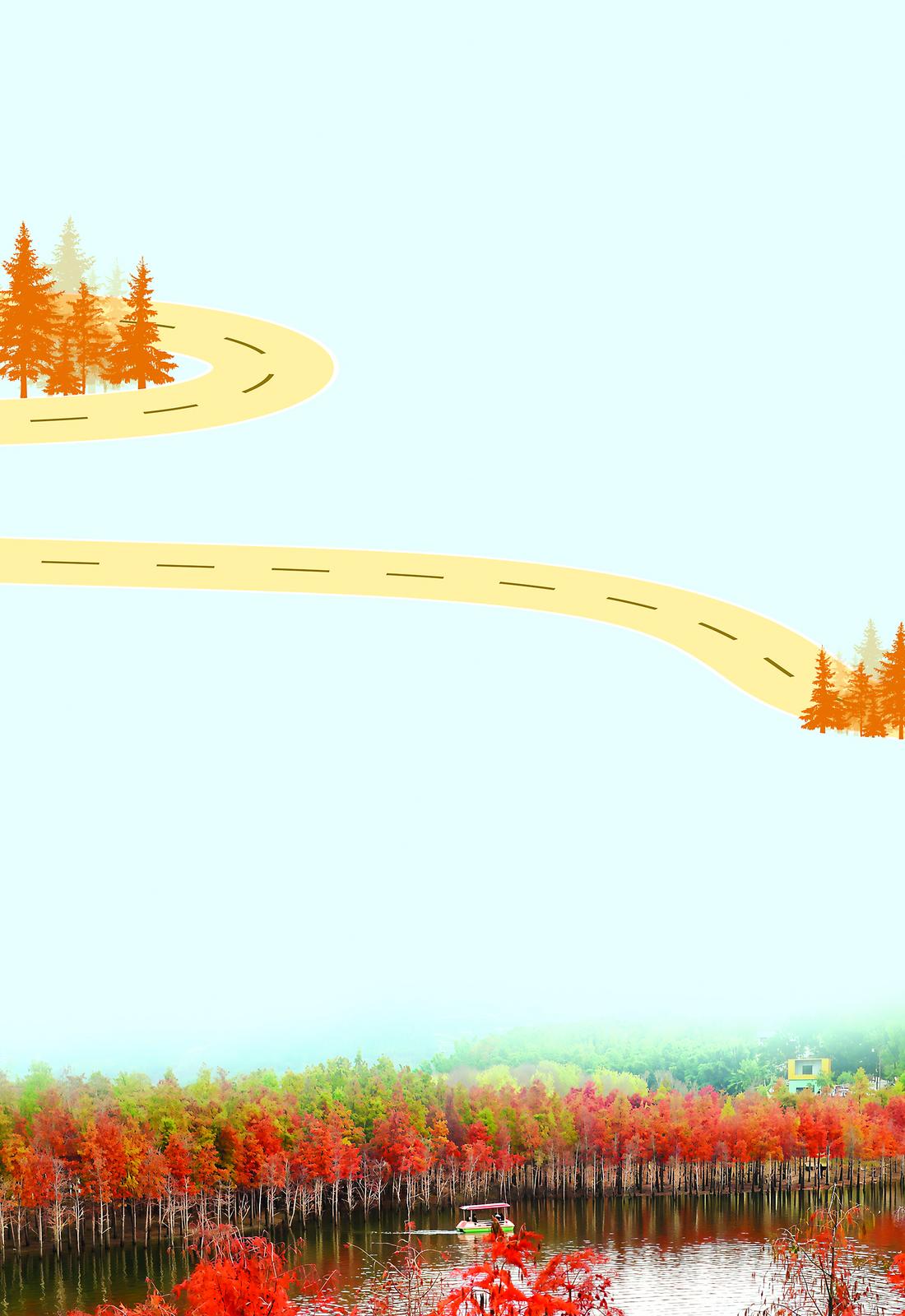
冬日落羽杉红似火(资料图片)
延平的山是绿绸子揉皱的,水是银链子晃碎的。但若要寻这方水土的魂,得去问那些在茫荡山里,在闽江岸边站成岁月刻度的树——它们把根扎进闽越的土里,把枝桠伸进秦汉的云里,用年轮写就一部会翻动的古书,它一年四季风姿绰约,把自己装扮成一帧帧精美的风景,定格了时光的流转。
茫荡山:“福建庐山”的婆娑身姿
“铜关卫士”
若说茫荡山三千八百坎的石阶,是锈满沧桑的记忆卷轴,那么在延平城区隐隐可见、高耸矗立的柳杉,便是守关的卫士。这些高可数丈的巨树,树皮皲裂如古鼎纹路,枝桠横斜似战旗翻卷,其中最年长的六棵柳杉已在此伫立千年。从前挑夫过坎,总爱抚摸它粗糙的躯干,道一句“摸过柳杉皮,脚底板生风”;如今游客仰头瞭望,只见浓荫里漏下碎金,树影在石阶上织成流动的网。山风掠过,松涛与杉叶的沙沙声混作一团,恍惚间,仿佛能听见这条闽赣古道上赶考士子激扬文字的谈笑声,亦能听见郑成功抗击清兵的马蹄声。柳杉是沉默的卫士,替素有“铜关”之称的延平,守住了岁月里的烟火与远方。
晴雨奇树
在茫荡山腹地的宝珠村,藏着一棵会“施法”的树。它的学名叫红豆杉,当地人却偏要给它取个更灵动的名字——“晴雨树”。这株高二十余米的古树,树干需四五人合抱,枝桠向四面铺开,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伞面下却藏着玄机:越是烈日当空,树下越会飘起蒙蒙雨丝。
我特意挑了大暑天去寻它。正午的日头把碎石路晒得发烫,刚步入树荫下,忽觉脖颈一凉。抬头望去,万千叶片间正凝着细密的水珠,阳光穿过叶缝,水珠折射出七彩光晕,随后“嗒”地坠下,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渐渐连成银丝,在地面织出流动的光斑。
树下歇脚的老翁呵呵笑道:“这树啊,是老天爷派来的偏心眼,专给宝珠村留着夏日的清凉。”有孩童在雨丝里追着光斑跑,笑声惊起几只山雀。我伸手去接那雨珠,凉丝丝的,带着草木的清甜——原来这雨不是水,是树的呼吸,是山的心事,是宝珠村藏在时光里的一首清凉的诗。
情侣樟树
茫荡山三楼村的古樟树最是深情。两株千年古樟相隔不过百步,树身需七八人合抱,树皮上的纹路像老人手背的青筋,却在离地三尺处骤然交缠——原来它们的根脉早就在地下织成了网,又在半空里让树冠挽成了穹顶。最老的那株胸径已达五米,年轮里藏着唐宋的月光;稍年轻的那株也有九百多岁,枝桠间飘荡着游客系下的红绸带。村民称其为“连理樟”,早年地质队勘探发现,它们的主根在地下两米处完全交融,宛如两只紧握的手。如今树下立着“夫妻树”的简介牌,常有情侣依偎着在树根上拍照,红绸带在风里飘成一片云霞。去年深秋我去时,见几位返乡的白发老人正围着树野餐,他们微笑着对我说“小时候在树洞里藏着小秘密,现在带着孙辈来寻。”古树不语,却把几代人的故事都酿成了树香。
竹柏森森
茫荡山溪源峡谷的竹柏,则是树中的“隐士”。沿着景区大门到溪源庵,十里清溪十里峡谷,到处可见竹柏,它们或成片成簇点染在廊桥、画亭,古道旁边,或列阵似地沿着峡谷山涧排开,其叶片细长如竹,却比竹多了几分温润;木质坚韧如柏,又比柏添了几缕清逸。当地人说,这里的竹柏“春不发躁,冬不枯槁”,像极了读了一辈子书的老夫子。我曾在暮春时节来访,山雾未散时,竹柏的新叶泛着翡翠色,叶尖悬着的水珠滴进溪里,泛起一圈圈的涟漪。不经意觅到峡谷深处有块卧石,刻着“竹柏之乡”四个隶体字,字迹被风雨磨得模糊,倒与竹柏的气质暗合——不事张扬,却把岁月熬成了风骨。
塔前菖上:秋天的童话
秋光漫过延平的山坳时,塔前菖上村的两棵银杏树便成了天地间最明亮的火把。这两株树冠参天的银杏树隔着丈许站立,树龄都有近千年,树干需六七个壮年人才能合抱。树皮皲裂如青铜鼎纹,枝桠均向东南倾斜,像是在朝村口的石板路鞠躬。
霜降一过,菖上村这两棵银杏树便会完成一场盛大的蜕变。墨绿的扇形叶先是镶上金边,继而通体洇成蜜蜡色,最后在某个清晨忽然全部转成金红。阳光穿过树冠时,枝叶间像浮着千万片颤动的金叶,风拂过时,满树叶子“沙沙”作响,不似萧瑟的秋声,倒像是无数细碎的铜铃在风中摇晃。最妙的是正午时分,日头正烈,树下的光斑竟不是寻常的圆形,而是银杏叶的形状,原来每片叶子都在筛滤阳光,把自己的轮廓拓印在青石板上,铺成满地跳动的小扇子。常有摄影爱好者架着炮筒般的相机蹲守在旁,只为等一场“黄金雨”。
当秋风卷着落叶掠过肩头,金黄的叶子乘着风势旋转而下,有的打着旋儿飘到溪涧里,随水流化作金色的小筏;有的落在阿婆晾晒的稻谷上,与谷粒的金黄融为一体;更多的则扑簌簌铺满地上,踩上去“咯吱”作响,像踩着一床蓬松的金丝被。孩子们最爱追着落叶跑,伸手去接那些盘旋的叶子,却总在指尖触到的前一刻被风掠走,惹得满场笑声与叶声缠绕成一团。
我曾在暮秋的黄昏坐在树下发呆,夕阳将树影拉得很长,两棵树的影子在地面交叠,宛如两只交握的手。有归鸟落在枝头,啄食着残留的白果,发出“笃笃”的轻响。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大抵就是这样。千年古树守着小小村落,金黄落叶拥着流动的时光,而我们都是偶然路过的旅人,在落叶纷飞时,撞见了时光最温柔的模样。
闽江:最忆斜溪那抹红绿
千年古榕
如果说茫荡山是延平高挺的脊梁,那么闽江便是延平奔腾向海的血脉。
在闽江上游的炉下镇斜溪村,闽江的水涨了又落,千年古榕却始终伫立岸头。它的主干要十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榕树根垂下来,粗的如巨蟒,细的如丝绦,把一亩多地都笼进了绿云里。村民说,这棵榕树下曾系过郑和下西洋的船缆,落过李侗、朱熹师徒讲学的书笺,听过抗战时期“闽江地下航线”的汽笛。我去的那天,有位白发阿婆坐在榕树根上簪花,她告诉笔者:“我爷爷的爷爷,就是在这棵树下娶的亲。”风过处,树根轻摇,仿佛在替古榕细数那些被江水带走的日子。它见过最汹涌的浪,也守着最绵长的暖。
落羽红杉
斜溪村的秋冬,是被树染出来的。
你看江面隆起的小岛上那一排排如霞似火的林子,这些原本披着墨绿羽衣的乔木,像被画师泼了朱砂,从树冠到枝梢,先是泛起橘黄,再洇成绯红,最后染成胭脂色。最妙的是临水而生的那一排,树干半浸在浅滩里,阳光斜照时,树影在水面铺成碎金红绸。常有摄影爱好者蹲在岸边等光影,说“落羽杉的红要配晨雾才绝”。破晓时分,薄雾从水面升起,红树若隐若现,恍如《山海经》里走出来的神树。
看看延平那些站在时光里的千姿百态的树,仿佛听到了松涛、杉语、竹吟、榕叹,在耳边织成一片绿潮。忽然明白,这些树岂止是草木?它们是延平的年轮,是光阴的证人,是刻在大地上的乡愁。当我们仰头看它们的枝桠刺破云层,其实是在回望自己的来处,那些被树影护过的童年,被落叶铺满的归程,被树荫藏起的故事,都在年轮里发了芽,长成了延平人血脉里的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