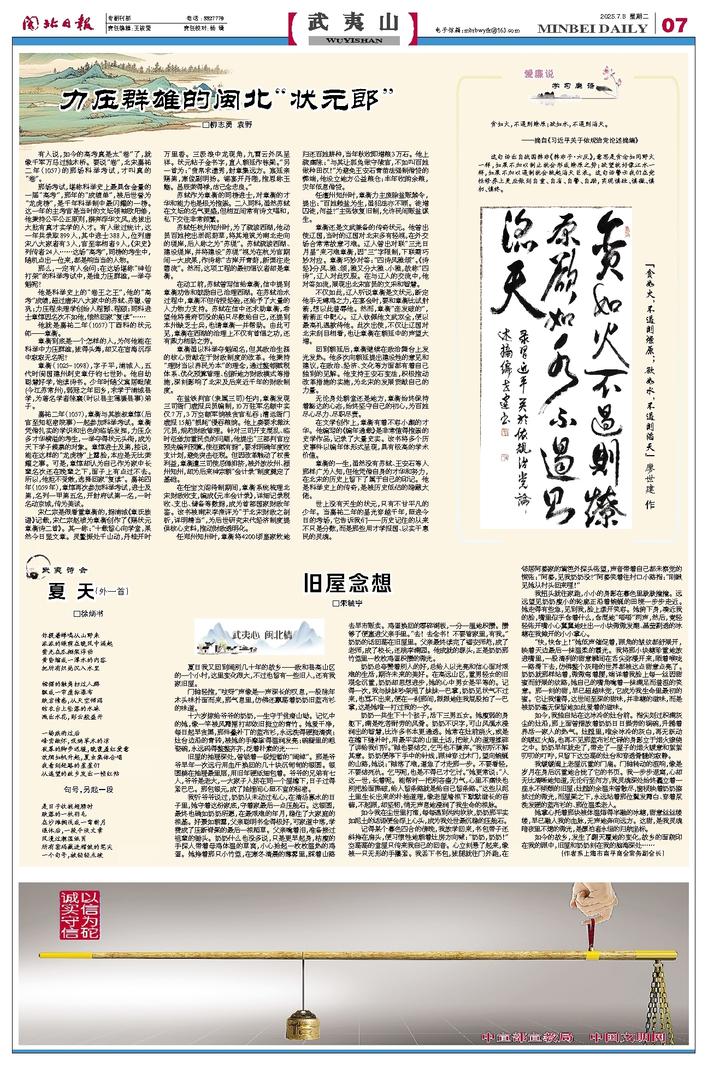夏日我又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政和县高山区的一个小村,这里变化很大,不过也留有一些旧人,还有我家旧屋。
门轴轻推,“吱呀”声像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一股陈年木头味扑面而来,那气息里,仿佛还飘荡着奶奶旧蓝布衫的味道。
十六岁嫁给爷爷的奶奶,一生守于贫瘠山坳。记忆中的她,像一竿被风霜捶打却依旧挺立的青竹。她爱干净,每日起早贪黑,那件叠补丁的蓝布衫,永远洗得硬挺清爽;灶台边沿的青砖,被她的手摩挲得温润发亮;碗橱里的粗瓷碗,永远码得整整齐齐,泛着朴素的光……
旧屋的抽屉深处,曾锁着一段短暂的“阔绰”。那是爷爷早年一次远行用血汗换回的几十块沉甸甸的银圆。银圆躺在抽屉最里层,用旧年硬纸细包着。爷爷的兄弟有七人,爷爷是老大,一大家子人挤在同一个屋檐下,日子过得紧巴巴。那包银元,成了妯娌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听爷爷说过,奶奶从未动过私心,在清汤寡水的日子里,她守着这份家底,守着家最后一点压舱石。这银圆,最终也确如奶奶所愿,在最艰难的年月,稳住了大家庭的根基。好景如朝露,父亲聪明书念得极好,可家道中落,学费成了压断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父亲噙着泪,准备接过祖辈的锄头。奶奶什么也没多说,只是更早起身,枯瘦的手探入带着母鸡体温的草窝,小心拾起一枚枚温热的鸡蛋。她挎着那只小竹篮,在寒冬清晨的薄雾里,踩着山路去早市贩卖。鸡蛋换回的零碎铜板,一分一厘地积攒。攒够了便塞进父亲手里。“去!去念书!不要管家里,有我。”奶奶的话回荡在旧屋里。父亲最终读完了福安师范,成了老师,成了校长,还桃李满园。他成就的源头,正是奶奶那竹篮里一枚枚鸡蛋积攒的微光。
奶奶总夸赞着别人的好,总给人以光亮和信心面对艰难的生活,期许未来的美好。在高远山区,重男轻女的旧观念沉重,奶奶却思想进步,她的心中男女是平等的。记得一次,我与妹妹吵架甩了妹妹一巴掌,奶奶见状气不过来,也骂不出来,便在一刹那间,狠狠地往我屁股拍了一巴掌,这是她唯一打过我的一次。
奶奶一共生下十个孩子,活下三男五女。她瘦弱的身躯下,满是吃苦耐劳的风骨。奶奶不识字,可山风溪水浸润出的智慧,比许多书本更通透。她常在灶前烧火,或是在檐下缝补时,用最平实的山里土话,把做人的道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贼也要结交,乞丐也不嫌弃。”我初听不解其意。奶奶便停下手中的针线,眼神穿过木门,望向蜿蜒的山路,她说:“贼落了难,逼急了才走那一步。不要看轻,不要结死仇。乞丐呢,也是不得已才乞讨。”她更常说:“人这一世,长着呢。能帮衬一把别吝啬力气,心里不痛快也别把脸面撕破,给人留条路就是给自己留条路。”这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朴拙道理,像老屋墙根下默默滋长的苔藓,不起眼,却坚韧,悄无声息地浸润了我生命的根脉。
如今我在尘世里打滚,每每遇到沟沟坎坎,奶奶那平实如泥土的话语便会浮上心头,成为我处世最沉稳的压舱石。
记得某个暮色四合的傍晚,我放学回来,书包带子还斜挎在肩头,便习惯性地朝着灶房方向喊:“奶奶,奶奶!”空荡荡的堂屋只传来我自己的回音。心立刻悬了起来,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我丢下书包,拔腿就往门外跑,在邻居阿婆家的篱笆外探头张望,声音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慌张:“阿婆,见我奶奶没?”阿婆笑着往村口小路指:“刚瞅见她从村头回来哩!”
我扭头就往家跑,小小的身影在暮色里跌跌撞撞。远远望见奶奶瘦小的轮廓正沿着蜿蜒的田埂一步步走近。她走得有些急,见到我,脸上漾开笑容。她俯下身,凑近我的脸,嘴里似乎含着什么,含混地“唔唔”两声,然后,竟轻轻张开嘴小心翼翼地吐出一小块微微发潮、晶莹剔透的冰糖在我摊开的小小掌心。
“快,快含上!”她低声催促着,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映着天边最后一抹温柔的霞光。我将那小块糖珍重地放进嘴里,一股清冽的甜意瞬间在舌尖弥漫开来,顺着喉咙一路滑下去,仿佛整个灰暗的世界都被这点甜意点亮了。奶奶就那样站着,微微弯着腰,端详着我脸上每一丝因甜蜜而舒展的纹路,她自己的嘴角噙着一抹满足而羞涩的笑意。那一刻的甜,早已超越味觉,它成为我生命里最初的蜜。它让我懂得,这世间至深的甜味,并非糖的滋味,而是被奶奶毫无保留地如此爱着的滋味。
如今,我独自站在这冰冷的灶台前。指尖划过积满灰尘的灶沿,那上面曾摆放着奶奶日日操劳的锅碗,升腾着养活一家人的热气。灶膛里,唯余冰冷的灰白,再无跃动的暖红火焰,也再不见那蓝布衫忙碌的身影立于烟火缭绕之中。奶奶早年就走了,带走了一屋子的烟火暖意和絮絮叨叨的叮咛,只留下这空荡的灶台和穿透骨髓的寂静。
我缓缓阖上老屋沉重的门扇。门轴转动的涩响,像是岁月在身后沉重地合拢了它的书页。我一步步退离,心却无比清晰地知道,无论行至何方,我灵魂深处始终矗立着一座永不倾颓的旧屋:灶膛的余温未曾散尽,窗棂映着奶奶擦拭过的微光,而屋梁之下,永远站着那位鬓发霜白、穿着浆洗发硬的蓝布衫的、那位温柔老人。
她掌心托着那块被体温焐得半融的冰糖,甜意丝丝缕缕,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无声地奔向远方。这甜,是我灵魂暗夜里不熄的微光,是漂泊者永恒的归航坐标。
如今的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乡的面貌印在我的眼中,旧屋和奶奶刻在我的脑海深处……
(作者系上海市南平商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