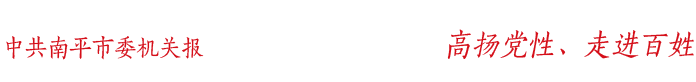白鹭来了,它们像来自蓬莱仙境的沉默舞者,又像游历江湖、浅吟低唱的诗人。它们以辽阔的苍穹为背景,以一首流传恒久的唐诗为引子,挟裹一股古朴之风翩跹而来。白鹭“不大不小、不胖不瘦、不长不短、不浓不淡、不艳不素”。为鹭不依附它物而生,崇尚自食其力,清清白白甘居烟雨一隅,并把曼妙身影连缀成诗歌,再用飞翔谱成悠然和畅的田园音符,这应是它的内心。
白鹭入诗,早在二千六百年前的先秦时期,就有古人描述和记载了。如诗经《国风·陈风·宛丘》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周颂·振鹭》之“振鹭于飞,于彼西雍”等。而唐宋时期留下脍炙人口的白鹭诗就更多了,如“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
诗人写白鹭,一般难免一个飞字,但白鹭也有生活之虞,它常以较多的时辰伫立于河边清滩,欲与芦花混为一色,只为一餐鱼味而守。你别看它纤细无比,捕食时的敏捷身手足以让你感叹。一条正在水中游弋的鱼,鳞片的银光才不小心地晃动了一下,就被它的一双锐眼瞥见。迅速计算好提前量的小白,毫不迟疑地一头扎入水中,从下水到搏斗,再到叼起猎物轰然出水,仅用去几秒钟工夫。其谋生本领,堪称一绝。
白鹭,自然界尤物。冬天,它们像披上婚纱的魔女,能让阡陌中的苦楝摇身变为开满白花的广玉兰。由娇小身躯站成的白色花骨朵,高高低低、疏疏密密、虚虚实实、亭亭玉立,俨然一场昭示生态之美的雅集。
有鹭鸥的水,一定是活水。在我客居的小河之畔,常见有人执竿垂钓。雨中,他们不再是青箬笠、绿蓑衣,而是撑着遮风挡雨的轻便雨伞。但白鹭还是当年西塞山前飞来的白鹭呵,倘若写《渔歌子》的张志和老先生隔空路过,不知仍否捋着胡须,长吟短咏一番。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亦垂丝”。
看来,为鹭之小白,比大诗人白居易更孤独、沉郁。因为它除了飞翔和捕食外,常常若有所思地呆立那里,它在想什么呢?有次去太湖采风,见过一只成年白鹭站立在高高的香樟树冠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远方。而其下方的枝丫上有窝刚出生的幼鹭,在张着小口、扇着猩红色的小翅膀嗷嗷待哺。每隔约一支烟的辰光,母鹭就会心灵感应地采食而来,为因饥饿而骚动的孩子们逐个口对口喂饲。原来,这只披着饰羽做了父亲的白鹭,在守护家人,为生活思考。
其实,白鹭的白,有别于白鹅、白头鸟的白。它应属于诗仙李太白的白、中国画留白的白。具体表现在: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杂念的纷扰。若在逆光下展翅于青绿之丛,洁白如雪的羽毛或被衬托得纤毫毕现。远远望去,宛若琪花玉树的枝叶、又如敬献于你的吉祥哈达,也好像“卧龙”手中代表智慧的羽扇。这眩目的、才被晨阳浸润过的那种纯粹,简直是对内心苍白和阴暗的控诉,它在赋予你诗情满怀的同时,又给你眼瞳审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