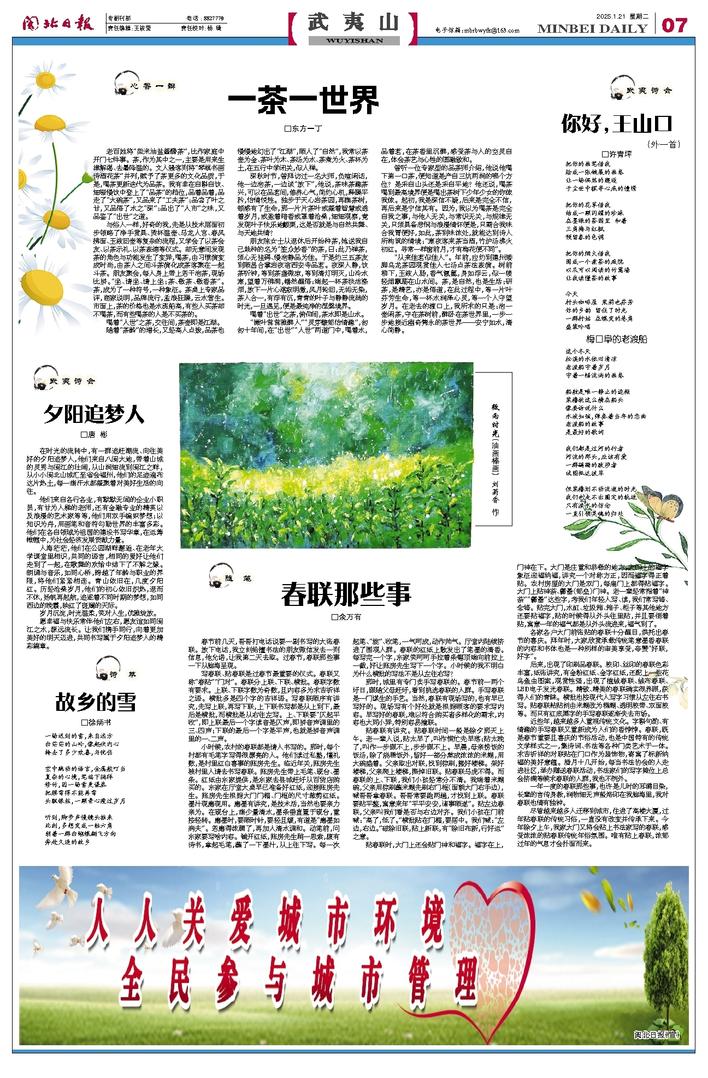春节前几天,哥哥打电话说要一副书写的大张春联。放下电话,我立刻给擅书法的朋友微信发去一则信息,他允诺,让我第二天去取。过春节,春联那些事一下从脑海呈现。
写春联、贴春联是过春节最重要的仪式。春联又称“春贴”“门对”。春联分上联、下联、横批。春联字数有要求。上联、下联字数为奇数,且内容多为求吉祈祥之语。横批多是四个字的吉祥语。写春联顺序有讲究,先写上联,再写下联,上下联书写都是从上到下,最后是横批,而横批是从右往左写。上、下联要“仄起平收”,即上联最后一个字读音是仄声,即拼音声调里的三、四声;下联的最后一个字是平声,也就是拼音声调里的一、二声。
小时候,农村的春联都是请人书写的。那时,每个村都有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的人。他们读过私塾,懂礼数,是村里红白喜事的账房先生。临近年关,账房先生被村里人请去书写春联。账房先生带上毛笔、砚台、墨条。红纸由东家提供,是东家去县城赶圩从百货店购买的。东家在厅堂大桌早已准备好红纸,迎接账房先生。账房先生根据大门门楣、门框的尺寸裁剪红纸。墨汁现磨现用。磨墨有讲究,是技术活,当然也要亲力亲为。在砚台上,滴少量清水,墨条垂直置于砚台,重按轻转。磨墨时,要顺时针,要轻且缓,有道是“磨墨如病夫”。若磨得浓稠了,再加入清水调和。动笔前,问东家要写啥内容。铺开红纸,账房先生稍一思索,腹有诗书,拿起毛笔,蘸了一下墨汁,从上往下写。每一次起笔、“旋”、收笔,一气呵成,动作帅气。厅堂内陆续挤进了围观人群。春联的红纸上散发出了笔墨的清香。每写完一个字,东家笑呵呵手拉着条幅顶端向前拉上一截,好让账房先生写下一个字。小时候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横批的写法不是从左往右写?
那时,城里有专门卖手写春联的。春节前一两个圩日,跟随父母赶圩,看到挑选春联的人群。手写春联是一门谋生的手艺。当然,春联有现场写的,也有早已写好的。现场写有个好处就是根据顾客的要求写内容。早写好的春联,难以符合购买者多样化的需求,内容也大同小异,特别容易撞联。
贴春联有讲究。贴春联时间一般是除夕那天上午。老一辈人说,贴太早了,叫作慌忙先早落;贴太晚了,叫作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早晨,母亲捞饭的饭汤,除了烧稀饭外,留好一部分熬成浓浓的米糊,用大碗盛着。父亲取出对联,找到棕刷,搬好楼梯。架好楼梯,父亲爬上楼梯,撕掉旧联。贴春联马虎不得。而春联的上、下联,我们小孩经常分不清。我端着米糊碗,父亲用棕刷蘸米糊先刷右门框(面朝大门右手边),喊哥哥拿春联。哥哥常要跑两趟,才找到上联。春联要贴平整,寓意来年“平平安安,诸事顺遂”。贴左边春联,父亲叫我们看是否与右边对齐。我们小孩在门前喊:“高了,低了。”横批贴在门楣,要居中。我们喊:“左边,右边。”破除旧联,贴上新联,有“除旧布新,行好运”之意。
贴春联时,大门上还会贴门神和福字。福字在上,门神在下。大门是庄重和恭敬的地方,大门上的福字象征迎福纳福,讲究一个对称方正,因而福字得正着贴。农村房屋的大门是双门,每扇门上都得贴福字。大门上贴神荼、鬱壘(郁垒)门神。老一辈经常指着“神荼”“鬱壘”这些字,考我们年轻人写、读,我们常写错、念错。贴完大门,水缸、垃圾箱、箱子、柜子等其他地方还要贴福字,贴的时候得从外头往里贴,并且要倒着贴,寓意一年的福气都是从外头流进来,福气到了。
各家各户大门前张贴的春联十分醒目,烘托出春节的喜庆。拜年时,大家欣赏承载传统笔意墨香春联的内容和书体也是一种别样的审美享受,夸赞“好联,好字”。
后来,出现了印刷品春联。胶印、丝印的春联色彩丰富,纸张讲究,有金粉红纸、金字红纸,还配上一些花鸟鱼虫图案,观赏性强,出现了植绒春联、绒布春联、LED电子发光春联。精致、精美的春联确实很养眼,获得人们的青睐。横批也按现代人写字习惯从左往右书写。贴春联粘贴剂由米糊改为糨糊、透明胶带、双面胶等。而只有红底黑字的手写春联逐渐失去市场。
近些年,越来越多人重视传统文化。字斟句酌、有情趣的手写春联又重新成为人们的香饽饽。春联,既是春节重要且喜庆的节俗活动,也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学样式之一,集诗词、书法等各种门类艺术于一体。求吉祈祥的对联贴在门口作为装饰物,寄寓了标新纳福的美好意蕴。腊月十几开始,每当书法协会的人走进社区,举办赠送春联活动,书法家们的写字摊位上总会挤满等候求春联的人群,我也不例外。
一年一度的春联那些事,也许是儿时的耳濡目染,长辈的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般烙印在我脑海里,我对春联也情有独钟。
尽管越来越多人迁移到城市,住进了高楼大厦,过年贴春联的传统习俗,一直没有改变并传承下来。今年除夕上午,我家大门又将会贴上书法家写的春联,感受浓浓的贴春联传统年俗氛围。唯有贴上春联,浓郁过年的气息才会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