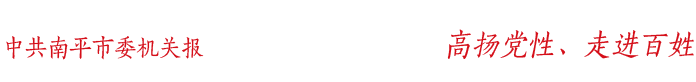文震亨在《长物志》里写道:“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从前读此句,只当是文人闲趣,直到去年才知这“邀”字里,藏着多少与天地的商量。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提过,他在西南联大时,宿舍窗台上总搁着几盆茉莉,夜里从图书馆回来,推开门便有清芬撞进衣襟。我原也爱这股子清冽,便从学校花圃中顺来两株栀子,想着在新租房阳台,利用房东留下的三五只花盆养一养,也能守着满室雪魂。谁料续后的日子原比想象中“野”——周一到周五,回乡下上班,常常端起浇花的陶壶时,已是一周工作时间。回城时,拉开阳台门,一片惨状不堪入目,吊兰在大花盆还好些,蔫巴巴地有气无力。栀子就严重脱水,叶子边缘发焦,像被谁用烟头烫烤了,整枝打蔫。嫩白的花苞未及绽放便皱成了小团,最后连根须都蜷成了枯柴,手指轻轻一碰,枯叶旋即凋落。我蹲在瓦盆前看残叶,忽然想起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他养兰,“朝灌夕溉,如养婴儿”,到底他那是在西湖边的暖阁里,而我阳台这里,只有穿堂风和零星的雨,更多是猛烈的日头。
自己都照顾不好,还想养花,老妻见了嘲讽道。痛定思痛,我转而种更“皮实”的活物。春上,街边有人兜售茄子、西瓜、洋茄以及辣椒苗。养不了花,我还不能种点蔬菜?于是,从街边买了两株朝天椒,待红果坠弯枝时的样子,倒也比花更热闹;又托人从老家带了几株玫瑰苗,想着“赠人玫瑰”的浪漫,总该比栀子好养些。头月倒真见着生机,辣椒苗抽出细针似的绿芽,玫瑰苞蕾裹着层毛茸茸的绿纱,连泥土缝里都钻出几簇蓝紫色的鸭跖草。我便每日坐在阳台一角,决意要看辣椒晒红了脸,数玫瑰苞上要裂开几道缝。偏是这“盼”字坏了事,平日里,我就给它们灌水,结果根须泡在泥里烂成一摊。原本绽放几朵白花的辣椒只剩几根光秆,玫瑰枯在枝头像团烧尽的纸,连鸭跖草都被我拔了——原是嫌它们“太野”喧宾夺主,坏了“规矩”。两月余,玫瑰彻底枯在盆里,成了邻居吊兰的肥料。辣椒仅剩一株,初绽的花朵萎了后,虽近两周不见开花了,但毕竟还绿着。
老妻又嫌弃了,说我不是那块料,弄脏阳台不说,还搭了时间。后来我索性懒了。听说,水养绿萝最省心,便张罗几节绿萝,插在粗陶瓶,和几个透明玻璃盆里。起初,只当它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每日路过时瞥一眼,见它叶子绿得发沉,茎秆软软垂着,倒像谁把春天揉碎了浸在水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隔三差五地瞅一眼,水浅浇一下,除此外,倒也清闲。
某夜下雨,我坐在阳台翻旧书,忽然发现阳台玻璃瓶里新抽的绿萝藤蔓正往水面探,嫩得能掐出水来的卷须,像婴儿攥着的小拳头。往后日子,由于我的近似不管不顾,它也倒真成了“不管不顾”的模样。阳光好时,叶片舒展成小荷叶;落雨时,水珠顺着藤蔓滚进瓶里。我渐渐发现,它从不需要“精心养护”,忘记换水时,水面浮着层薄膜样的脏灰,叶子却更绿。偶尔忘了搬动,被晒得蔫了,浇两杯水又缓过来。最妙的是梅雨季,藤蔓顺着阳台栅栏爬开来,绿得要滴出油来,倒像是替我把整个春天都挂在了阳台上。
从阳台剪几秆藤,分养在矿泉水瓶,摆在床头,房间里也似乎有了生气。原来,我这粗糙的性子,只能种粗糙的植物。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写过莫高窟的壁画:“那些线条,原是画工在黑暗里一笔笔刻进岩壁的,他们并不知道,千年后会有灯光照亮。”日子久了,绿萝忽然让我懂了些类似的道理——从前总想着“养”花,要给它最好的土、最适时的水、最周全的护,却忘了花本是天地间的活物,要的是一场“不较劲”的缘分。就像汪曾祺的茉莉,文震亨的兰草,原不是靠“精心设计”活下来的,是风来了就摇,雨落了就润,该开时便开,该谢时便谢,倒比人间的“刻意”更接近生命的本真。
如今,阳台那盆绿萝已经肆无忌惮伸出远了,墨绿的叶还挂着今早的露珠。我常望着它想:生活的道理,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费力”的活计里——不必非要种出惊艳的花,不必执着于“成功”的结果,能在岁月里稳稳当当活下来,已是天地最大的仁慈。就像此刻,风穿过,绿萝的藤蔓轻轻晃了晃,像在说:“你看,活着,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