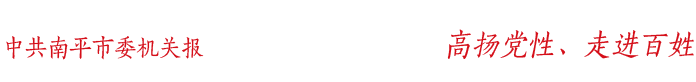菜市场的角落堆起了紫红的“小山”。人工改良的杨梅有着讨喜的模样,果肉厚实质感丰盈,咬破的瞬间,红色的汁水在口腔里迸发,甜意裹着微酸在舌尖化开,果核小,吃完掌心只留下淡淡的果香。
回忆老家屋后的山里,野生杨梅树曾是夏日里最诱人的存在。小时候,暑假刚开始,我便跟着奶奶和母亲钻进山林。盛夏的大山像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林木青翠欲滴,野花肆意绽放,红的、白的、蓝的、紫的,在风里摇晃,鸟雀的啼鸣与蜂蝶的振翅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满是草木与泥土的清新。
我们循着酸香,常能寻到半人高的杨梅“窝子”。玻璃珠大小的果实密密麻麻地挤在枝头,生青的挂着白霜,半红的透着羞怯,熟透的则红得发亮。轻轻摘下一颗送入口中,酸爽的滋味瞬间“攻占”味蕾,牙齿忍不住打颤,却又情不自禁伸手去够下一颗。翻过山头,总能遇见更红艳的杨梅树,我们爬完一山又一山,背篓渐渐沉了,裤子上沾满了草屑,奶奶的山歌也在山涧里飘,时光就在这走走停停中浸满了山野的芬芳。
回到家,奶奶和母亲将背篓里的杨梅小心翼翼地倒在竹编晒盘里,分拣的过程像在完成一场仪式。个大熟透的直接洗净生吃,汁水顺着嘴角流淌,饱满带粉的撒上白砂糖腌渍,或用冰糖慢炖后吃。母亲会挑些红透的小杨梅给爷爷泡酒,透明的酒坛里渐渐浮起一抹诱人的绛红,而奶奶则忙着处理未熟的杨梅,一部分做成杨梅酱,另一部分则制成杨梅干。
杨梅酱的制作是门讲究的手艺。先将杨梅洗净去杂,放入未沾油的铁锅,加入山泉水小火慢熬,直到果肉与果核分离。再用纱布细细过滤,留下的果汁继续熬煮,直到变成浓稠的黑褐色。冷却后装入玻璃瓶,那是天然的消暑良药,夏日舀一勺加冰糖冲饮,酸甜生津;扁桃体发炎时涂抹患处,或是胃疼时兑水内服,都有奇效。即便酱料凝结成块,泡化后依旧带着时光沉淀的醇厚。
奶奶制作的杨梅干很是一绝。她先用盐水浸泡,沥干后入锅加冰糖慢熬,不用加水,果肉里的汁水会渐渐渗出,熬出的汤汁能直接当饮品喝。剩下的杨梅用大火收干汁水,再放在太阳下晒至微皱,最后撒上白糖封存。每当食欲不振或嘴馋时,奶奶就会笑眯眯地取出一小把,那酸甜的滋味在口中化开,像含着一口浓缩的夏日阳光。
长夏炎热时,母亲又送来一篮野杨梅。看着紫红的果实,鼻尖仿佛又飘来山野间的酸香,眼前浮现出奶奶熬酱时灶台上升腾的热气,母亲分拣杨梅时专注的神情,还有自己蹲在晒盘边偷吃杨梅的模样。这小小的果实,裹着梅雨季节的湿润,藏着山野寻梅的乐趣,更盛着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每一口香甜,都是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