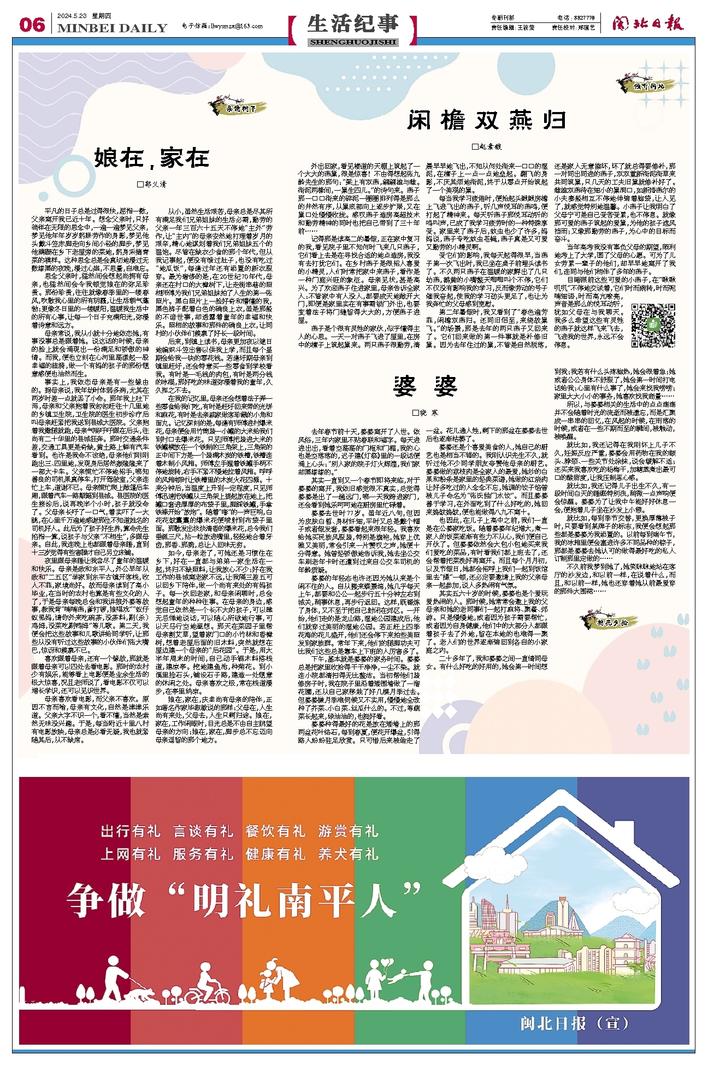平凡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屈指一数,父亲离开我已近十年。想念父亲时,只好徜徉在无限的思念中,一遍一遍梦见父亲,梦见他年年岁岁躬耕劳作的身影,梦见他头戴斗笠赤脚走向乡间小径的脚步,梦见他蹒跚在乡下老屋旁的菜地,躬身采摘青菜的模样。这种思念总是会真切地漫过无数漆黑的夜晚,漫过心扉,不思量,自难忘。
思念父亲时,猛然间会想起尚拥有母亲,也猛然间会令我顿觉娘在的弥足珍贵。那份珍贵,往往就像春季里的一缕春风,吹散我心里的所有阴霾,让生活朝气蓬勃;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温暖我生活中的所有心事,让每一个日子充满阳光,弥漫着诗意和远方。
母亲常说,我从小就十分地依恋她,有事没事总是跟着她。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就会涌现出一份满足和骄傲的神情。而我,便也立刻在心河里荡漾起一股幸福的涟漪,做一个有妈的孩子的那份惬意感便也油然而生。
事实上,我依恋母亲是有一些缘由的。据母亲说,我年幼时体弱多病,尤其在两岁时差一点就丢了小命。那年我上吐下泻,母亲和父亲抱着我匆匆赶往十几里地的乡镇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初步诊疗后叫母亲赶紧把我送到县城大医院。父亲抱着我撒腿就跑,母亲气喘吁吁跟在后头,往尚有二十华里的县城狂奔。那时交通条件差,交通工具更是奇缺,黄土路上鲜有汽车看到。也许是我命不该绝,母亲他们刚刚跑出三、四里地,发现身后居然轰隆隆来了一部大卡车。父亲慌忙不停地招手,哪知善良的司机果真停车,打开驾驶室,父亲连忙上车,道谢不已。母亲慌忙爬上敞篷后车厢,跟着汽车一路颠簸到县城。县医院的医生接诊后,说再晚半个小时,孩子就没命了。父母亲长吁了一口气,着实吓了一大跳,在心里千万遍地感谢那位不知道姓名的司机好人。此后为了孩子好生养,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孩子与父亲“不相生”,多跟母亲。自此,我连晚上也都跟着母亲睡,直到十三岁觉得有些害臊才自己另立床铺。
夜里跟母亲睡让我尝尽了童年的温暖和快乐。母亲是政和东平人,外公早年从政和“二五区”举家到东平古镇开客栈,收入不菲,家境尚好。故而母亲读到了高小毕业,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有些文化的人了,于是母亲每晚总会和我讲狼外婆等故事,教我背“喃喃燕,爹打锣,娘唱戏”“蚁仔蚁虱妈,请你外来吃碗茶,没茶料,剔(杀)鸡姆,没菜吃剔鸭姆”等儿歌。第二天,我便会把这些故事和儿歌讲给同学听,让那些从没有听过这些故事的小伙伴们张大嘴巴,惊讶和羡慕不已。
喜欢跟着母亲,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跟着母亲可以四处去看电影。那时的农村少有娱乐,能够看上电影便是业余生活的极大惊喜,况且老师说了,看电影不仅可以增长学识,还可以见识世界。
母亲喜欢看电影,而父亲不喜欢。原因不言而喻,母亲有文化,自然是津津乐道。父亲大字不识一个,看不懂,当然是索然无味没兴趣。于是,每当附近十里八村有电影放映,母亲总是必看无疑,我也就紧随其后,从不缺席。
从小,虽然生活艰苦,母亲总是尽其所有满足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必需,勤劳的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地“主外”劳作,让“主内”的母亲安然地打理着岁月的艰辛,精心地谋划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的温饱。尽管在缺衣少食的那个年代,但从我记事起,便没有饿过肚子,也没有吃过“地瓜饭”,每逢过年还有添置的新衣服穿。最为奢侈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母亲还在村口的大樟树下,让走街串巷的照相师傅为我们兄弟姐妹拍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一脸好奇和懵懂的我,黑色裤子配着白色的确良上衣,虽是那般的不谙世事,却透露着童年的幸福和快乐。照相的故事和那件的确良上衣,让同村的小伙伴们羡慕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到镇上读书,母亲更加夜以继日地编织斗笠出售以供我上学,而且每个星期会给我一块的零花钱。若逢圩期母亲到镇里赶圩,还会特意买一些零食到学校看我。有时是一毛钱的肉包,有时是两分钱的冰棍,那好吃的味道弥漫着我的童年,久久挥之不去。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还会想着法子弄一些零食给我们吃,有时是赶圩回来带的光饼和麻花,有时是去亲戚家做客珍藏的小角和面丸。记忆深刻的是,每逢有师傅进村爆米花,母亲便会用竹筒装一小罐的大米给我们到村口去爆米花。只见师傅把装进大米的铁罐横放在一个铁制的三角架上,三角架的正中间下方是一个装满木炭的铁槽,铁槽连着木制小风箱。师傅左手握着铁罐手柄不停地旋转,右手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呼呼的风箱顿时让铁槽里的木炭火花四溅。十来分钟后,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只见师傅迅速把铁罐从三角架上提起放在地上,把罐口套进厚厚的布袋子里,脚踩铁罐,手拿铁棒开始“放炮”。随着“嘭”的一声巨响,白花花鼓囊囊的爆米花便喷射到布袋子里面。那散发出淡淡清香的爆米花,总令我们垂涎三尺,拈一粒放进嘴里,轻轻地合着牙齿,那香、那脆,总让人回味无穷。
如今,母亲老了,可她还是习惯住在乡下,好在一直都与弟弟一家生活在一起,终归不缺照料,让我放心不少;好在我工作的县城离老家不远,让我隔三差五可以回乡下陪伴,做一个尚有来处的有妈孩子。每一次回老家,和母亲闲聊时,总会想起童年的种种往事。在母亲的身边,感觉自己依然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话,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可以天马行空地遐想。那天在菜园子里帮母亲割艾草,望着家门口的小竹林和香樟树,想着老屋后面的旧木料,突然就想在屋边建一个母亲的“后花园”。于是,用大半年周末的时间,自己动手锯木料搭栈道,建凉亭。挖地建鱼池,种菊花。到小溪里捡石头,铺设石子路,建造一处惬意的休闲之处。母亲喜欢之极,常在栈道漫步,在亭里纳凉。
娘在,家在,庆幸尚有母亲的陪伴,正如著名作家毕淑敏说的那样: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娘在,家在,工作闲暇时,目光总是不由自主眺望母亲的方向;娘在,家在,脚步总不忘迈向母亲逗留的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