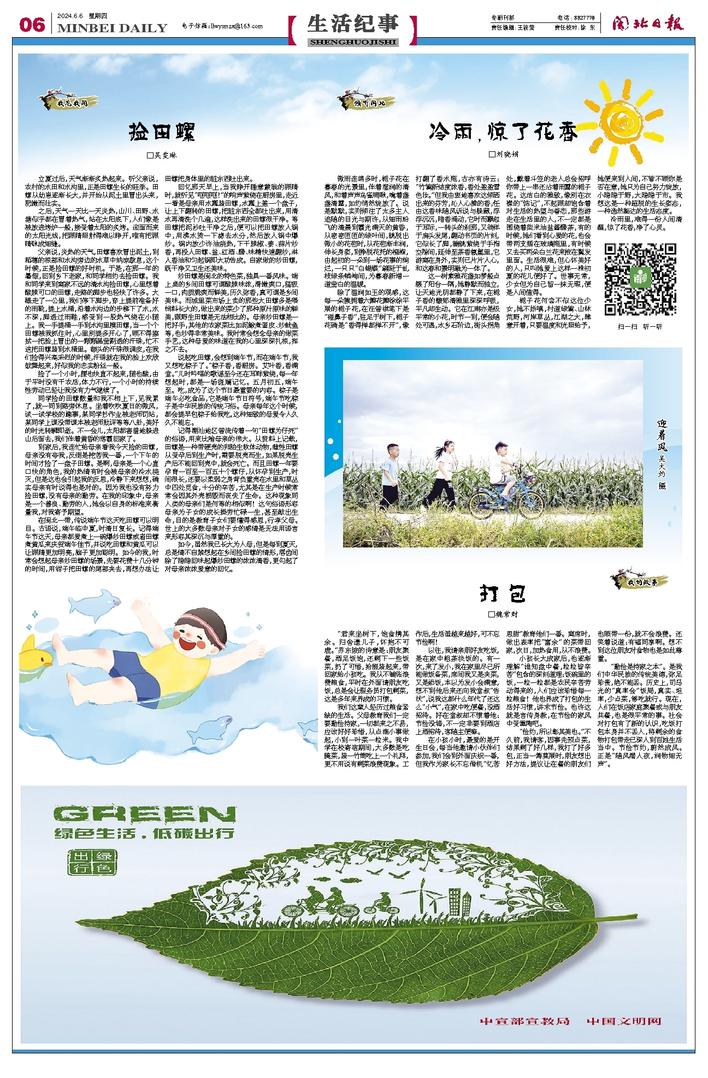立夏过后,天气渐渐炙热起来。听父亲说,农村的水田和水沟里,正是田螺生长的旺季。田螺从幼崽逐渐长大,并开始从泥土里冒出头来,肥嫩而壮实。
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山川、田野、水塘似乎都在冒着热气,站在太阳底下,人们像是被放进烤炉一般,接受着太阳的炙烤。迎面而来的太阳光线,把眼睛照射得难以睁开,唯有把眼睛眯成细缝。
父亲说,炎热的天气,田螺喜欢冒出泥土,到稻穗的根部和水沟旁边的水草中纳凉歇息,这个时候,正是捡田螺的好时机。于是,在那一年的暑假,回到乡下老家,和同学相约去捡田螺。我和同学来到离家不远的清水沟捡田螺,心里想着酸辣可口的田螺,走路的脚步也轻快了许多。大概走了一公里,我们停下脚步,穿上提前准备好的雨靴,提上水桶,沿着水沟边的步梯下了水,水不深,脚透过雨鞋,感受到一股热气绕在小腿上。我一手提桶一手到水沟里摸田螺,当一个个田螺被我抓住时,心里别提多开心了,顾不得擦拭一把脸上冒出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汗珠,忙不迭把田螺装到水桶里。额头的汗珠很调皮,在我们捡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汗珠就在我的脸上欢欣鼓舞起来,好似我的忠实粉丝一般。
捡了一个小时,腰也快直不起来,腿也酸,由于平时没有干农活,体力不行,一个小时的持续性劳动已经让我没有力气继续了。
同学捡的田螺数量和我不相上下,见我累了,就一同到路旁休息。坐着吹吹夏日的微风,谈一谈学校的趣事,某同学抄作业被老师罚站,某同学上课没带课本被老师批评等等八卦,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不一会儿,太阳都害羞地躲进山后面去,我们伴着黄昏的落霞回家了。
到家后,我连忙给母亲看我今天捡的田螺,母亲没有夸我,反倒是挖苦我一番,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捡了一盘子田螺。是啊,母亲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角色,我的热情有时会被母亲的冷水浇灭,但是这也会引起我的反思,冷静下来想想,确实母亲有时说得也是对的。因为我也没有努力捡田螺,没有母亲的勤劳。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她会以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对我寄予期望。
在闽北一带,传说端午节这天吃田螺可以明目。古语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记得端午节这天,母亲都爱煮上一碗爆炒田螺或者田螺煮黄瓜来庆贺端午佳节,并说吃田螺和黄瓜可以让眼睛更加明亮,脑子更加聪明。如今的我,时常会想起母亲炒田螺的场景,先要花费十几分钟的时间,用钳子把田螺的尾部夹去,再想办法让田螺把身体里的脏东西吐出来。
回忆那天早上,当我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时,就听见“哐哐哐!”的响声萦绕在厨房里,走近一看是母亲用水瓢装田螺,水瓢上盖一个盘子,让上下翻转的田螺,把脏东西全都吐出来,用清水再清洗个几遍,这样洗出来的田螺很干净。等田螺把泥沙吐干净之后,便可以把田螺放入锅中,用沸水烫一下滤去水分,然后放入锅中爆炒。锅内放少许油烧热,下干辣椒、姜、蒜片炒香,再投入田螺、盐、红酒、醋、味精快速翻炒,淋入香油和匀起锅即大功告成。自家做的炒田螺,既干净又卫生还美味。
炒田螺是闽北的特色菜,独具一番风味。端上桌的乡间田螺可谓酸辣味浓,滑嫩爽口,猛吸一口,肉质脆爽而鲜美,历久弥香,真可谓是乡间美味。而城里菜市场上卖的那些大田螺多是喂饲料长大的,做出来的菜少了那种原汁原味的鲜美,跟野生田螺是无法相比的。母亲炒田螺是一把好手,其他的农家菜比如泥鳅煮蛋皮、炒鱿鱼等,也炒得非常美味。我时常会想念母亲的做菜手艺,这种母爱的味道在我的心里深深扎根,挥之不去。
说起吃田螺,会想到端午节,而在端午节,我又想吃粽子了。“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儿时吟唱的歌谣至今还在耳畔萦绕,每一年想起时,都是一场斑斓记忆。五月初五,端午至。吃,成为了这个节日最重要的内容。粽子是端午必吃食品,它是端午节日符号,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母亲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提早包粽子给我吃,这种细致的母爱令人久久不能忘。
记得潮汕地区曾流传着一句“田螺为仔死”的俗语,用来比喻母亲的伟大。从资料上记载,田螺是一种带硬壳的卵胎生软体动物,雌性田螺从受孕后到生产时,需要脱壳而生,如果脱壳生产后不能回到壳中,就会死亡。而且田螺一年要孕育一百至一百五十个螺仔,从怀孕到生产,时间很长,还要以柔弱之身背负重壳在水里和草丛中四处觅食,十分的辛苦,尤其是在生产时候常常会因其外壳损毁而丧失了生命。这种现象同人类的母亲们是何等的相似啊!这句俗语形容母亲为子女的成长操劳忙碌一生,甚至献出生命,目的是教育子女们要懂得感恩,行孝父母。世上的大多数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其深沉与厚重的。
如今,虽然我已长大为人母,但是每到夏天,总是情不自禁想起在乡间捡田螺的情形,唇齿间除了隐隐回味起爆炒田螺的浓浓清香,更勾起了对母亲浓浓爱意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