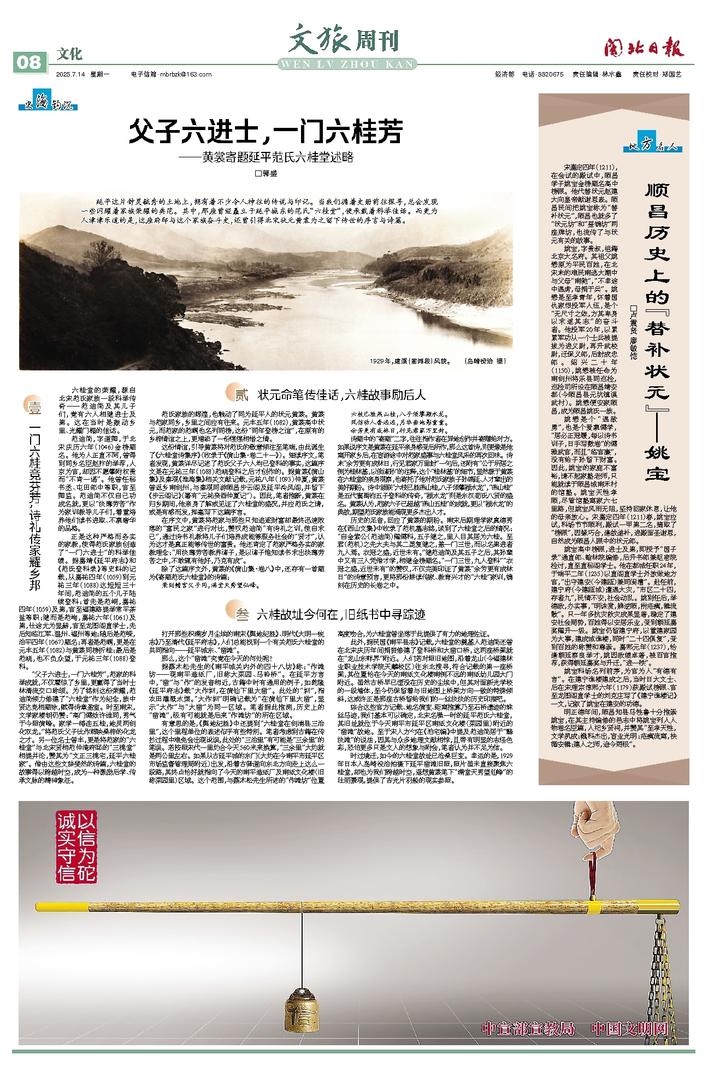延平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拥有着不少令人神往的传说与印记。当我们循着史册前往探寻,总会发现一些闪耀着家族荣耀的典范。其中,那座曾经矗立于延平城东的范氏“六桂堂”,便承载着科举佳话。而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这座府邸与这个家族奋斗史,还曾引得北宋状元黄裳为之留下传世的序言与诗篇。
壹 一门六桂竞芬芳,诗礼传家耀乡邦
六桂堂的荣耀,源自北宋范氏家族一段科举传奇——范迪简及其儿子们,竟有六人相继进士及第。这在当时是轰动乡里、光耀门楣的佳话。
范迪简,字道卿,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金榜题名。他为人正直不阿,曾得到同乡名臣赵抃的举荐,入京为官,却因不愿攀附权贵而“不肯一谒”。他曾任秘书丞、屯田郎中等职,官至卿监。范迪简不仅自己功成名就,更以“淡薄劳苦”作为家训教导儿子们,着重培养他们读书进取、不慕奢华的品格。
正是这种严格而务实的家教,使得范氏家族创造了“一门六进士”的科举佳绩。据嘉靖《延平府志》和《范氏登科录》等史料的记载,从嘉祐四年(1059)到元祐三年(1088)这短短三十年间,范迪简的五个儿子陆续登科:首先是范峒,嘉祐四年(1059)及第,官至福建路提举常平茶盐等职;继而是范峋,嘉祐六年(1061)及第,仕途尤为显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先后知临江军、温州、福州等地;随后是范嵘,治平四年(1067)题名;再者是范嵎,更是在元丰五年(1082)与黄裳同榜折桂;最后是范峣,也不负众望,于元祐三年(1088)登科。
“父子六进士,一门六桂芳”,范家的科举成就,不仅震惊了乡里,更赢得了当时士林清流交口称颂。为了铭刻这份荣耀,范迪简倾力修建了“六桂堂”作为纪念,族中贤达竞相题咏,赋得诗章盈室。时至南宋,文学家楼钥仍赞:“高门儒效许谁同,秀气于今照演峰。家学一椿连五桂,地灵两剑化双龙。”将范氏父子比作辉映桑梓的化龙之才。另一位名士曾丰,更是将范家的“六桂堂”与北宋贤相范仲淹府邸的“三槐堂”相提并论,赞其为“文正三槐宅,延平六桂家”。借由这些文辞斐然的诗篇,六桂堂的故事得以跨越时空,成为一种激励后学、传承文脉的精神象征。
贰 状元命笔传佳话,六桂故事励后人
范氏家族的辉煌,也触动了同为延平人的状元黄裳。黄裳与范家同乡,乡里之间应有往来。元丰五年(1082),黄裳高中状元,而范家的范嵎也名列同榜,这份“同年登榜之谊”,在原有的乡梓情谊之上,更增添了一份惺惺相惜之情。
这份情谊,引导黄裳将对范氏的敬意倾注至笔端,由此诞生了《六桂堂诗集序》(收录于《演山集·卷二十一》)。细读序文,笔者发现,黄裳详尽记述了范氏父子六人均已登科的事实,这篇序文是在元祐三年(1088)范峣登科之后才创作的。据黄裳《演山集》及秦观《淮海集》相关文献记载,元祐八年(1093)仲夏,黄裳曾返乡南剑州,与秦观同游顺昌步云阁及延平泠风阁,并留下《步云阁记》(署有“元祐癸酉仲夏记”)。因此,笔者推断,黄裳在归乡期间,他亲身了解或见证了六桂堂的盛况,并应范氏之请,或是有感而发,挥毫写下这篇序言。
在序文中,黄裳将范家与那些只知追逐财富却最终迅速败落的“富民之家”进行对比,赞叹范迪简“有诗礼之训,使自求己”,通过诗书礼教将儿子们培养成能够服务社会的“贤才”,认为这才是真正能够传世的富贵。他还肯定了范家严格务实的家教理念:“用淡薄劳苦教养诸子,是以诸子惟知读书求出淡薄劳苦之中,不敢辄有他好,乃克有成”。
除了这篇序文外,黄裳的《演山集·卷八》中,还存有一首题为《寄题范氏六桂堂》的诗篇:
荣到蟾宫父子同,满堂天秀望仙峰。
六枝已胜燕山桂,八子须攀颍水龙。
风信动人香远远,月华垂地影重重。
余芳更有成林日,行见君家万里封。
诗题中的“寄题”二字,往往指作者在异地创作并寄赠给对方。如果说序文是黄裳在延平亲身感受后所作,那么这首诗,则更像是他离开家乡后,在宦游途中对范家盛事与六桂堂风采的再次回味。诗末“余芳更有成林日,行见君家万里封”一句后,还附有“公于所居之侧为桂林基,以俟诸孙”的注释,这个“桂林基”的细节,显然源于黄裳在六桂堂的亲身观察,也寄托了他对范氏家族子孙绵延、人才辈出的美好期盼。诗中颔联“六枝已胜燕山桂,八子须攀颍水龙”,“燕山桂”是五代窦禹钧五子登科的传奇,“颍水龙”则是东汉荀氏八贤的盛名。黄裳认为,范家六子已超越“燕山五桂”的成就,更以“颍水龙”的典故,期望范氏家族能涌现更多杰出人才。
历史的足音,回应了黄裳的期盼。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在《西山文集》中收录了范机墓志铭,谈到了六桂堂之后的情况:“自金紫公(范迪简)擢儒科,五子继之,里人目其居为六桂。至君(范机)之先大夫与其二昆复继之,盖一门三世,而以名第进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继范迪简及其五子之后,其孙辈中又有三人凭借才学,相继金榜题名。“一门三世,九人登科”“衣冠之盛,近世未有”的赞叹,不仅完美印证了黄裳“余芳更有成林日”的诗意预言,更将那份耕读传家、教育兴才的“六桂”家训,镌刻在历史的长卷之中。
叁 六桂故址今何在,旧纸书中寻踪迹
打开那些积满岁月尘埃的南宋《舆地纪胜》、明代《大明一统志》乃至清代《延平府志》,人们总能找到一个有关范氏六桂堂的共同指向——延平城东、“凿滩”。
那么,这个“凿滩”究竟在今天的何处呢?
据蔡木松先生的《南平城关内外的四十八坊》称:“作滩坊——现南平造纸厂,旧称大菜园、马铃桥”。在延平方言中,“凿”与“作”的发音相近,古籍中时有通用的例子,如乾隆《延平府志》载“大作圳,在演仙下里大凿”。此处的“圳”,指农田灌溉水渠。“大作圳”明确记载为“在演仙下里大凿”,显示“大作”与“大凿”为同一区域。笔者据此推测,历史上的“凿滩”,极有可能就是后来“作滩坊”的所在区域。
有意思的是,《舆地纪胜》中还提到“六桂堂在剑浦县三治里”,这个里程单位的表述似乎有些特别。笔者考虑到古籍在传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讹误,此处的“三治里”有可能是“三余里”的笔误。若按照宋代一里约合今天560米来换算,“三余里”大约就是两公里左右。如果从古延平城的东门(大约在今南平市延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附近)出发,沿着古驿道向东北方向走上这么一段路,其终点恰好就指向了今天的南平造纸厂及南纸文化楼(旧称菜园里)区域。这个范围,与蔡木松先生所述的“作滩坊”位置高度吻合,为六桂堂曾坐落于此提供了有力的地理佐证。
此外,据民国《南平县志》记载,六桂堂的奠基人范迪简还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捐资修建了登科桥和大凿口桥,这两座桥梁就在“龙山东畔界”附近。人们若对照旧地图,沿着龙山(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天麟校区)往东北搜寻,符合记载的第一座桥梁,其位置恰在今天的南纸文化楼南侧不远的南纸幼儿园大门附近。虽然古桥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其对面新光学校的一段墙体,至今仍保留着与旧地图上桥梁方向一致的特殊倾斜,这或许正是那座古桥留给我们的一丝淡淡的历史印痕吧。
综合这些官方记载、地名演变、距离推算乃至石桥遗迹的蛛丝马迹,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北宋名噪一时的延平范氏六桂堂,其旧址就位于今天南平市延平区南纸文化楼(菜园里)附近的“凿滩”故地。至于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提及范迪简居于“黯淡滩”的说法,因其与众多地理文献相悖,且带有明显的志怪色彩,恐怕更多只是文人的想象与附会,笔者认为并不足为信。
时过境迁,如今的六桂堂故址已沧桑巨变。幸运的是,1929年日本人岛崎役治拍摄下延平凿滩旧照,照片虽未直接聚焦六桂堂,却也为我们跨越时空,遥想黄裳笔下“满堂天秀望仙峰”的壮丽景观,提供了吉光片羽般的现实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