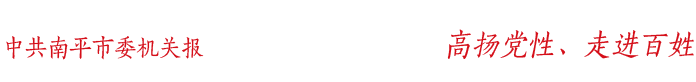家乡的老茶,如同儿时记忆中走乡串户货郎担上的叮叮糖与家里厨房横梁上悬挂的老腊肉,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心头上。
我的老家在建溪河畔,小乡村山环水绕,气候温润极适宜种茶,溪岸边漫山遍野的都是茶园,这里出产的绿茶和茉莉花茶远近闻名,乡人种茶卖茶,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家每户的饭桌旁、灶台上,都少不了一个粗瓷茶壶,每当有亲朋好友来串门,主人总会热情地用壶盖奉上一杯茶,这是淳朴乡人应有的待客之道。
乡人喝的大多数是自家炒制的老茶。每年清明前后,村里的妇女耕山队采了两道嫩叶后,勤劳的农妇便将修剪剩下的老叶带回家,细心挑拣除去腐烂、变质及带有虫眼、蛛丝的茶叶,晾晒去水分后,在灶里燃起小火用大铁锅炒茶,茶叶的质量全凭经验把控。在炒制过程中,需用手指来回翻炒,并不断揉捻,确保锅中的茶叶能够充分卷曲并均匀受热。当锅中飘出诱人的茶香时,可慢慢熄灭柴火直至叶色由绿变为青黑后,即可起锅。此时茶叶色泽较为均匀,香气扑鼻,凉透后,用粗瓷罐可长久存放。
母亲当年是妇女耕山队的一员,队里管护着近千亩茶园,清明前后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日子。白天采茶、晾晒,隔一段时间晚上就要集中炒茶。当时茶厂离家较远,小路沿途只有寥寥几户人家,炒茶半夜收工时,乡人早已熄灯睡觉,到处黑漆漆、静悄悄的,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狗叫声引得附近几家的狗跟着狂吠,自告奋勇打着火把去接母亲回家的我,吓得胆战心惊火把前后乱舞,总感觉狗要向我扑来的情形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母亲在村里茶厂炒茶练就了手艺,对火候和色泽的掌控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在家里炒茶当然得心应手。用心挑选,精心晾晒,细心炒制,自然成茶的色泽味深受邻里和家人的好评。
父亲最爱喝母亲炒制的茶,每次新茶炒好后,总是迫不及待地烧水泡茶尝鲜,评点着今年茶的味道。他常说茶苦涩之后是回甘,人生就和茶一样,会苦一阵子,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一阵子的苦,最终却苦了一辈子,你们是苦一阵子还是苦一辈子,就看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了。还好,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把父亲意味深长的这句话牢记在心里,先后走出了大山。
物资匮乏的年代,用以盛茶的器物,家里有三两个开水壶和行军壶的并不多见,粗瓷茶壶倒是家家必备,还是不少人家流传几代人的老物件,用这些老茶壶泡出的茶,味道特别醇厚。
那时候,乡亲们去田里或是上山劳作携带大茶壶出门自然不便,用竹筒装茶水就成了首选。家家户户基本都有几个用老竹或是新竹制成的竹筒,老竹筒经久耐用,新竹筒味道清新,就看你的选择了。在田里在山上劳作久了,累了渴了,汗流浃背地走到阴凉处,拿起放置在那儿的竹筒,拨开塞子凑到嘴边,一抬手,“咕咚咕咚”,清凉的茶水猛灌入喉,顷刻间顿感累渴不再,那份畅爽、那份惬意、那份享受,只有经此劳作的人才会有这深切的体验。
有时从田里或是地里干活回来,饿极了等不及母亲煮饭,便从木桶饭甑里盛一碗剩饭,用茶壶里的茶汤冲泡,伴随着清清淡淡又有一丝的甜味,三两下一碗饭就下肚了。
炒制的老茶经年之后,便成为了陈茶。陈茶的味道醇厚,口感独特,优质的陈茶,品饮起来感觉就像在与一位长者智者会话,波澜不惊却让人心灵通透。明崇祯进士周亮工在《闽茶曲》中这样评价陈茶,“雨前虽好但嫌新,火气未除莫接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
陈茶除了口感极好外,其药理作用也是非常明显,具有暖胃祛寒,消食减肥,降虚火等功效。乡人多将陈茶存在粗瓷罐里,隔潮隔热,温度适宜,取用方便,以备家中不时之需。
“人间清醒,喝茶要紧”。我对于饮茶的习惯,正是源于这家乡的老茶。此后,随着岁月的流转和生活的变迁,无论喝茶的方式、茶叶的种类和档次如何变化,烙刻在我的记忆最深处的,还是那端起大茶壶盖或是手持竹筒酣畅淋漓尽兴而饮的场景,那真叫一个爽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