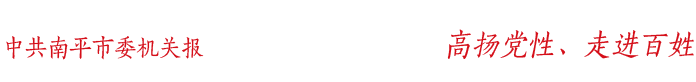《摆渡人》是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创作的小说,作者从少年的角度洞悉人性的温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所见所感,道出所有人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终极幸福的向往。书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追问:“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那么谁将是你灵魂的摆渡人?”
摆渡人,从狭义解释就是在渡口码头用船为人家提供交通服务的人。广义也可解读为,生命中的没有过多交集的匆匆过客,或生命中曾经帮助、援助扶助过你的人。深层次的意义则是:在红尘的渡口,把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用快乐、善良与爱,抵抗并超脱这个世界的悲伤、孤独与无助。
所谓灵魂的摆渡人,话题太大太沉重,倒真的要提一提海岸、河岸、湖岸的摆渡人,这是一个很乡愁很有烟火味道的名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家乡因为建电站,形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人工湖,于是就有了很多很多的渡口与摆渡人。小时候去乡下、走亲戚、回老家,必经渡口,必须摆渡。一湾清水,一叶扁舟,风中雨中,东岸西岸,摇摇摆摆的青荇,遮不住远山的青黛,水路上,眼前雾气茫茫,身后流水悠悠。“远去远去,坐着小船,张起一面帆,点亮一盏灯,老人的渔歌,响彻江面。”那时的旅途很是浪漫,那时的走亲很有诗意,那时的生活很温馨。乡愁,就像一条无边无际的河,载着我们通往老家的祖屋,通往出发的远方。
很久很久以前,摆渡一直都是此岸与彼岸居民交换货物、采办食品的“生命航线”。不知不觉间,我们见多了“天堑”变“通途”。去对岸、去湖心、去海岛,也没了渡口,更无须渡轮。随着“遇水搭桥、逢山开路”的壮举,壮观的钢构大桥向着每一条江河湖海无限地伸长,所向披靡,无所畏惧,而与此同时,渡口与摆渡人则“大踏步”地缩减,只能躲藏于最原始、最荒僻的乡野、村寨。大桥越来越壮观,道路越来越宽广,摆渡越来越少见。
十多年前,曾去过平潭岛出差。那时,上岛得经过娘宫码头轮渡,人与车都得排队一个多小时才能上渡轮。我有意去船头的驾驶室好奇地观察着半机械的“摆渡人”左舵右舵。船速慢得让人感觉要驶向天涯海角,到了海岛却别有洞天,行走于远离都市更原始更生态的礁石、海岸与古城,有着与陆地完全不同的惊艳与体验。后来,再次来到娘宫码头,已不见当年的忙碌和喧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拉客声。如今只剩几艘靠泊的铁皮船,诉说着往日的沧海桑田,在大大的“拆”字面前,显得有些安静和萧条。这里早已成为文化的符号,在时光中慢慢老去。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据统计,现如今全省摆渡人不足千人。如果要近距离地观摩摆渡及摆渡人,只能去旅游的人造景点,或者寻找儿时的模糊记忆。
“彼岸,烟波流转,可有人寻我?对岸,繁华三千,可有人候我?摆渡人早已随风而去 踽踽独行,不得归航。”虽然,在庞大的现代科技面前,没有一条江河是不可逾越的,但我无法忘怀没有桥的岁月。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靠着摆渡人渡人渡河,一摇一摆、一心一意地向着对岸,那可是行的方向、形的支柱、心的皈依。
今年六月,朋友相约延平。在华灯初上的夜晚,幸得当地挚友的精心安排,特意请了一位老摆渡人横渡闽江。裹挟着闽江水湿润的气息,一叶舟,一盏灯,一轮明月,一个摆渡人,穿越时空,仿佛驶入了某个被遗忘的旧梦,一时间竟有些时空交错的恍惚,辨不清今夕何夕,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可惜,对岸已寻不到渡口,找不着可以系缆的凭依,最后只能原路返回,徒留一丝怅惘在江风里低回。
现实中,如此浪漫、如此梦幻的此岸彼岸,只是一种“独特”的体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刻意”的经历已非常态,更非理性。但有形的摆渡人,可以稀缺,无形的摆渡人却不可或缺,我们之所以需要他们,不仅仅是要找回那渐行渐远的乡愁与平静平淡的岁月,更是让心与灵抵达彼岸,实现既优雅又快捷的生命价值与人生目标。
浮生有如陌上红尘,身若扁舟,踯躅于岁月深处,寻找心灵的渡船,虽说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但行路难,心路亦艰,起落无凭,进退失据,唯愿苍茫的渡口有更多的摆渡人,点破迷雾,指引归途,为每一份疲惫的“靠岸之心”,寻得一块可以系缆的青石;为每一缕渴望栖息的“停泊之意”,拢住一片无风无浪的港湾,护佑那风雨兼程的孤帆,驶向平安与温暖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