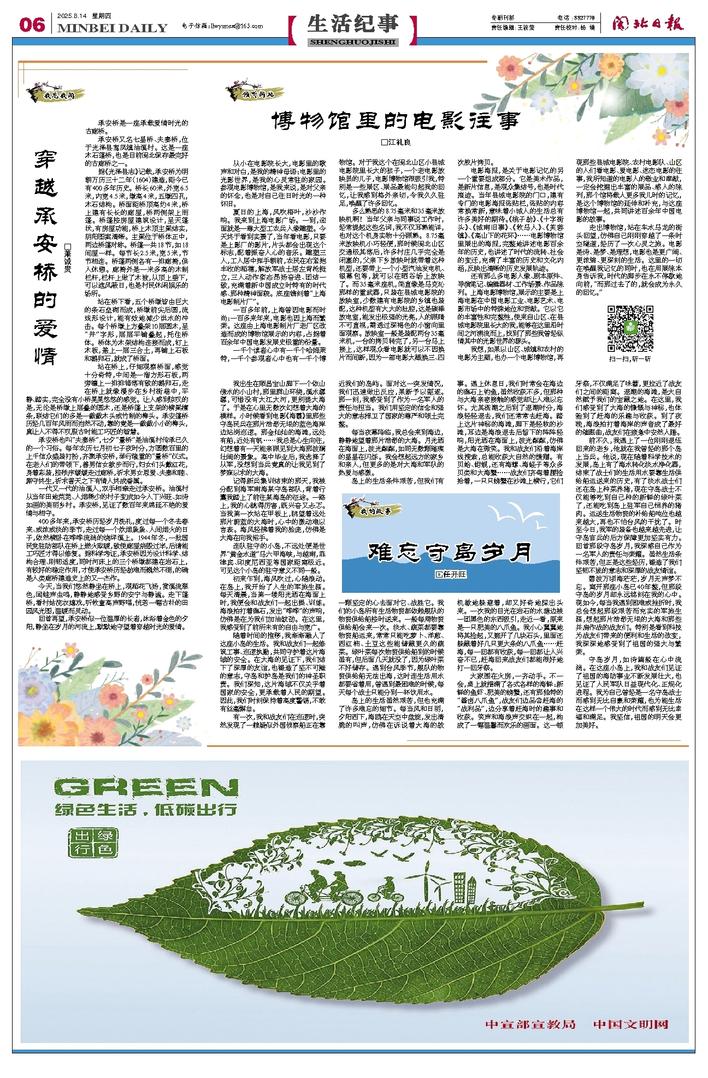从小在电影院长大,电影里的歌声和对白,是我的精神母语;电影里的光影世界,是我的心灵常驻的家园。参观电影博物馆,是我来说,是对父亲的怀念,也是对自己往日时光的一种怀旧。
夏日的上海,风吹梧叶,沙沙作响。我来到上海电影广场。一到,迎面就是一尊大型工农兵人像雕塑。今天终于看到实景了,当年看电影,只要是上影厂的影片,片头都会出现这个标志,配着振奋人心的音乐。雕塑三人,工人居中挥手朝前,农民在右紧抱丰收的稻穗,解放军战士居左背枪挺立,三人动作姿态昂扬奋进、团结一致,充满着新中国成立时特有的时代感、那种精神面貌。底座镌刻着“上海电影制片厂”。
一百多年前,上海曾因电影而时尚;一百多来年来,电影也因上海而繁荣。这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展示的内容,占据着百余年中国电影发展史极重的份量。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参观者心中也有一千个博物馆。对于我这个在闽北山区小县城电影院里长大的孩子,一个老电影放映员的儿子,电影博物馆很吸引我,特别是一些展区、展品最能勾起我的回忆,让我感到格外亲切,令我久久驻足,唤醒了许多回忆。
多么熟悉的8.75毫米和35毫米放映机啊!当年父亲与同事说工作时,经常提起这些名词,我不仅耳熟能详,也对这个机身实物十分眼熟。8.75毫米放映机小巧轻便,那时候闽北山区交通极其落后,许多村庄几乎完全是闭塞的,父亲下乡放映时就带着这种机型,还要带上一个小型汽油发电机、银幕包等,就可以在晒谷场上放映了。而35毫米座机,简直像是马克沁那样的重武器,只装在县城电影院的放映室,少数建有电影院的乡镇也装配,这种机型有大大的肚腔,这是碳棒放电室,能发出极强的光亮,人的眼睛不可直视,需透过深褐色的小窗向里面观察。放映室一般是装配两台35毫米机,一台的拷贝转完了,另一台马上接上,这样观众看电影就可以不因换片而间断,因为一部电影大概换三、四次胶片拷贝。
电影海报,是关于电影记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美术作品,是新片信息,是观众集结号,也是时代痕迹。当年县城电影院的门口,建有专门的电影海报张贴栏,张贴的内容常换常新,意味着小城人的生活总有许多美好的期待。《桃子劫》、《十字街头》、《城南旧事》、《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电影博物馆里展出的海报,完整地讲述电影百余年的历史,也讲述了时代的流转、社会的变迁,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反映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
还有那么多电影人像、剧本原件、导演笔记、编辑器材、工作场景、作品陈列。上海电影博物馆,展示的主要是上海电影在中国电影工业、电影艺术、电影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它以它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使来自山区、在县城电影院里长大的我,能够在这里沿时间之河溯流而上,找到了那些我曾经纵情其中的光影世界的源头。
我想,如果以山区、城镇和农村的电影为主题,也办一个电影博物馆,再现那些县城电影院、农村电影队、山区的人们看电影、爱电影、迷恋电影的往事,我所知道的电影人的敬业和奉献,一定会挖掘出丰富的展品、感人的陈列,那个馆将载入更多我儿时的记忆,是这个博物馆的延伸和补充,与这座博物馆一起,共同讲述百余年中国电影的故事。
走出博物馆,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回望,仿佛自己刚刚穿越了一条时空隧道,经历了一次心灵之旅。电影是诗、是梦、是理想,电影也是更广阔、更浓缩、更深刻的生活。这里的一切在唤醒我记忆的同时,也在用展陈本身告诉我,时代的脚步在永不停歇地向前,“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永久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