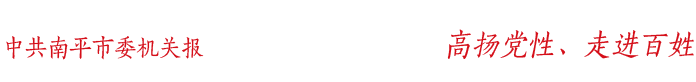我的故乡是一个小村落,三面的山,流淌着四季的溪水,浇绿过一年又一年的老杨树。暮色四合时分,我站在老屋旧址的土地上,晚风掠过空荡荡的宅基地,卷起几片枯黄的杨树叶,在残垣断壁间打着旋儿。恍惚间,那株依偎在大门前的老杨树又立在了眼前,挺拔的树干舒展开绿色的伞,枝叶间漏下的斑驳陆离在门当的青石上跳跃,仿佛时光倒流回了三十年前等待父母归来的黄昏。
老屋的大门处在院墙的东南,门板的黑漆在经年累月中渐渐剥落,只有门环上的铜绿还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东侧墙根外,老杨树的虬根半漏在地面,像爷爷布满皱纹的手,深深抠进路面的夯土里。父亲说,老杨树是爷爷盖屋时亲手栽下的,算来比我还大两辈人哩。春寒料峭的清晨,我常看见父亲披着藏青色外套给老树浇水,水珠顺着树皮滑落,在冻土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像一串串未干的泪痕。
老杨树最懂春的脚步,总比别家的树早一些带给我们春天的信。当北风还在呼啸,它就憋着一股劲儿从灰色的枝丫里迸出星点绿芽。起初像是绣娘失手打翻的紫褐色墨水,待春风一吹,那些朦胧的紫褐色便渐渐褪成鹅黄,最后舒展成翡翠般的嫩叶。放学路上,我们总会掰下一段细长又光滑的枝条,用手一拧,树皮便和枝干分离,凑在唇边一吹,呜哇呜哇的哨音惊飞了檐下的麻雀,惊醒了打盹的老黄牛,整个村子便充满了春天的歌声。
盛夏的雷雨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乌压压的云层重重叠叠,呼的一阵狂风,先是稀稀疏疏的小雨点,继而豌豆粒般的大雨点,然后雨点成线,刹那间已是瓢泼大雨,整个世界便成了明晃晃的一片水帘。狂风撕扯着老杨树的枝干,发出呜呜的哀鸣,雨点砸在叶片上溅起银色的雾。我蹲坐在堂屋的木门内,听着树干吱呀吱呀作响,时刻担心着这棵经年的老树会被连根拔起。渐渐地,风停了,雨小了,母亲撩开窗帘,指着院外安然无恙的老树说:“瞧见没?树疤子都裂开了嘴,可腰杆子还笔直呢。”果然,那些伤痕累累的枝条上,新生的嫩绿在暴雨的冲刷下愈发显得鲜亮。
老树是位忠实的守门人,清晨我们背着布书包,蹦蹦跳跳地向村小走去,炊烟袅袅,老杨树在朦胧中更显挺拔。一个个暮色浸染的黄昏,老杨树都是我们的等候站,我总喜欢趴在门挡旁的青石上,姐姐则抱着缀满兰花的蓝布书包靠在老树旁。她数着树皮上横向凸起的纹路,说这是老树记录年龄的密码。知了在最高的枝头上拉长了音,一群麻雀掠过,抖落的羽毛轻轻飘下。姐姐指着树皮上凹陷的疤痕说:“你看,去年的老疤已经长出新肉了哩。”那是老树守护着家的印记:拉着山石的拖拉机,超载的车斗从树干上擦过,刺耳的摩擦声撕裂了黄昏的宁静……我伸手抚摸那圈凸起的痂,粗糙的触感里竟带着温热的生命力。母亲说:“老树那是在守护着咱家,不然撞坏的可就是咱家的门楼子了……”
老伙计护着老屋四十多年,也在我的记忆里茂盛了十几年,后来老屋拆迁,老树也走过了自己的一生,成为了新房某块梁木,我总觉得遗憾,没能最后再看他一眼,无数个清晨与黄昏,新房的屋子里,似乎隐隐传来老家伙的呢喃。偶尔经过老屋旧址,总会蹲下抚摸龟裂的土地。泥土深处,或许还埋着半截断根,会在某个春日里,冒出鲜嫩的芽。恍惚间,那个在杨树下听蝉鸣、吹树笛的少年又回来了,他踮脚想够最高处的嫩芽,衣袖沾满杨絮,笑声惊飞了整片天空的飞鸟。
暮色渐深,晚风送来远处工厂的汽笛声。我知道老杨树永远活在了记忆深处,它把年轮刻进我的掌纹,将守护织进我的梦境。当春风再度掠过空荡的宅基地,我仿佛听见她沙沙地说:“娃呀,别忘了,每个春天都从破土的新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