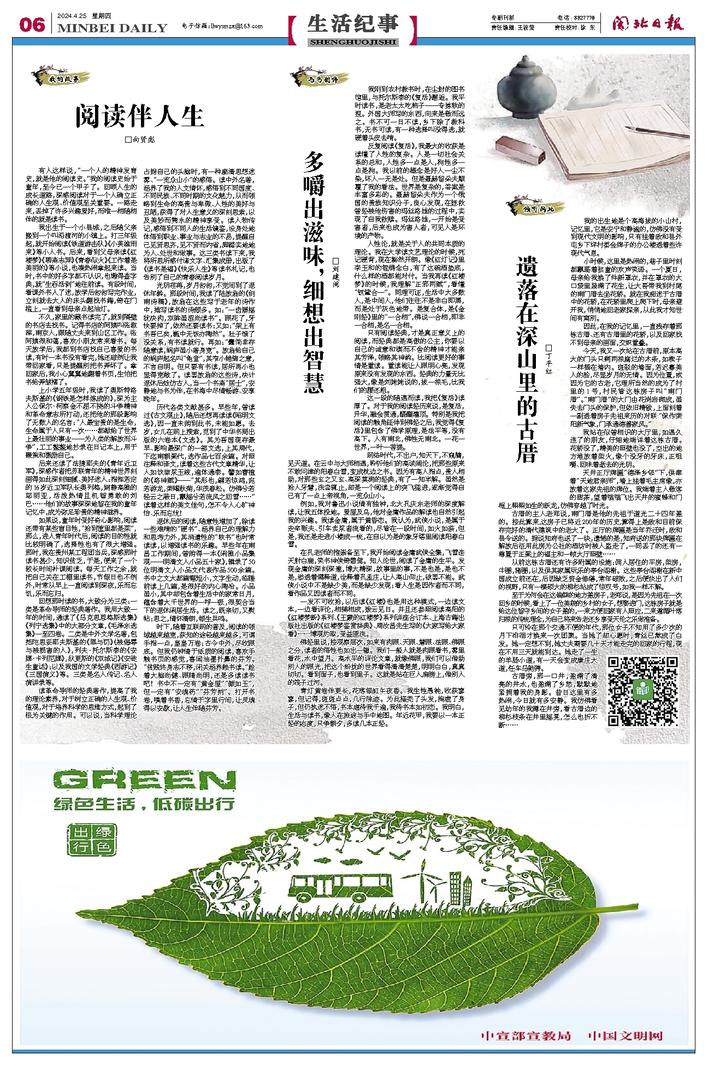我刚到农村教书时,在尘封的图书馆里,与托尔斯泰的《复活》邂逅。我平时读书,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外国大师写的东西,向来是敬而远之。书不可一日不读,乡下除了教科书,无书可读,有一种选择叫没得选,就硬着头皮去啃。
反复阅读《复活》,我最大的收获是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多一点是人,狗性多一点是狗。我以前的概念是好人一尘不染,坏人一无是处。但是聂赫留朵夫颠覆了我的看法。世界是复杂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聂赫留朵夫作为一个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良心发现,在拯救曾经被他伤害的玛丝洛娃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玛丝洛娃,一开始是受害者,后来也成为害人者,可见人是环境的产物。
人性论,就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我在大学读文艺理论的时候,死记硬背,现在豁然开朗。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铿锵念白,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当我再读《红楼梦》的时候,我理解“正邪两赋”,看懂“钗黛合一”。同理可证,生活中大多数人,是中间人,他们往往不是非白即黑,而是处于灰色地带。是复合体,是《金刚经》里的“一合相”,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只有阅读经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而经典都是高傲的公主,你要以自己的诚意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亲其芳泽,领略其神韵。比阅读更好的事情是重读。重读能让人眼明心亮,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经典的力量无比强大,像是刘姥姥说的,拔一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
这一段的随遇而读,我把《复活》读厚了。对于我的阅读经历来说,是复活,升华,融会贯通,醍醐灌顶。特别是我把阅读的触角延伸到佛经之后,我觉得《复活》里包含了佛学原理,是法平等,没有高下。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网络时代,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在云中与大师相遇,聆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把那些原来不敢问津的阳春白雪,变成枕边之书。因为有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对那些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经典,有了一知半解。虽然是拾人牙慧,浅尝辄止,却是一个阅读上的突飞猛进,逐渐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上帝视角,一览众山小。
例如,我对鲁迅小说情有独钟,北大孔庆东老师的深度解读,让我五体投地。爱屋及乌,他对金庸作品的解读也自然引起我的兴趣。我读金庸,属于黄昏恋。我认为,武侠小说,是属于走卒贩夫、引车卖浆者流看的,尽管在一段时间,如火如荼,但是,我还是走进小楼成一统,在自以为是的象牙塔里阅读阳春白雪。
在孔老师的推崇备至下,我开始阅读金庸武侠全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知人论世,阅读了金庸的生平。发现金庸的深刻深邃,博大精深,故事里的事,不是也是,是也不是,渗透着儒释道,诠释着孔孟庄,让人高山仰止,欲罢不能。武侠小说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
一发不可收拾,以后读《红楼》也是用这种模式,一边读文本,一边看评论,相辅相成,拨云见日。并且还参照阅读高阳的《红楼梦断》系列、《王蒙的红楼梦》系列讲座合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鉴赏辞典》、周汝昌先生写的《大家写给大家看》……博观约取,受益匪浅。
佛经里说,按观察层次,如来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分,读者的悟性也如出一辙。我们一般人就是肉眼看书,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高水平的评论文章,就像佛眼,我们可以借助别人的眼光,把这个纷扰的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看到面子,也看到里子。这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借别人的筏子过河。
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缸午夜香。我生性愚钝,收获寥寥,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为此搔秃了头发,掏虚了身子,但仍执迷不悟,书本虐待我千遍,我待书本如初恋。我明白,生活与读书,像人在旅途与手中地图。年近花甲,我要以一本正经的态度,只争朝夕,多读几本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