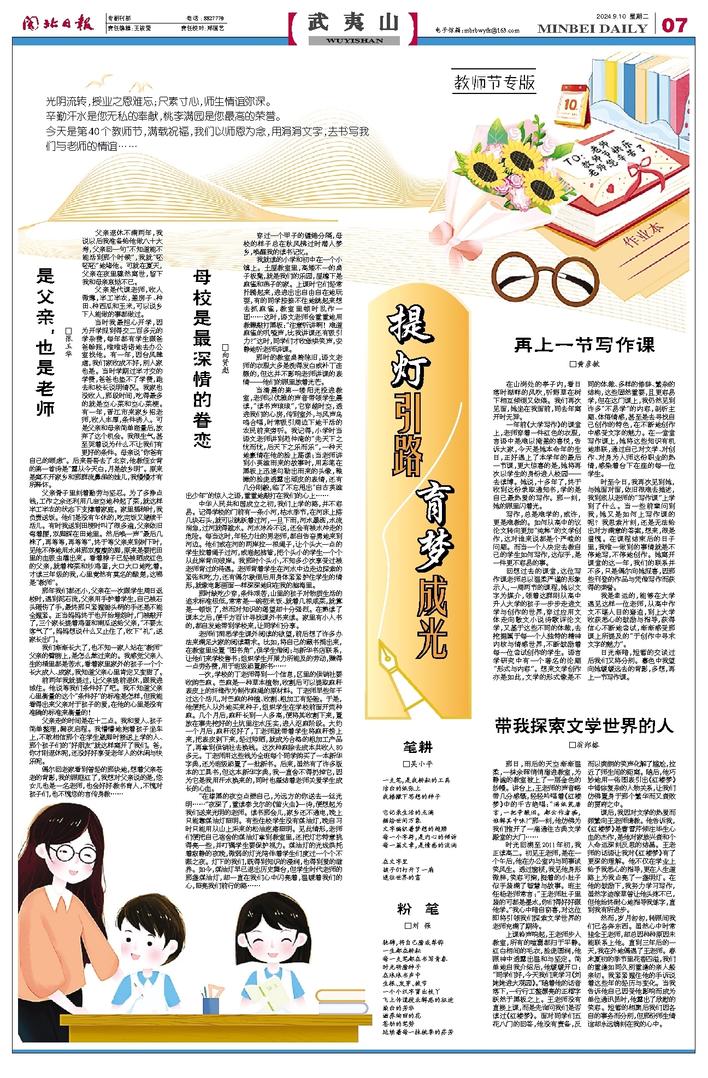穿过一个甲子的缱绻分隔,母校的样子总在秋风拂过时潜入梦乡,唤醒我的读书记忆。
我就读的小学和初中在一个小镇上。土屋教室里,高矮不一的桌子板凳,就是我们的乐园,屋檐下是麻雀和燕子的家。上课时它们经常扑腾起来,进进出出自由自在地玩耍,有的同学按捺不住地跳起来想去抓麻雀,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这时,语文老师会重重地用教鞭敲打黑板:“注意听讲啊!难道麻雀的叽喳声,比我讲课还有吸引力?”这时,同学们才收敛哄笑声,安静地听老师讲课。
那时的教室桌椅陈旧,语文老师的衣服大多是洗得发白或补丁连缀的,但这并不影响老师讲课的表情——他们的眼里放着光芒。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投进教室,老师以优雅的声音带领学生晨读,“读书声琅琅”,它穿越时空,透进我们的心房,传到室外,与风声鸟鸣合唱,时常吸引周边下地干活的农民前来旁听。我记得,小学时当语文老师讲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种天地豪情在他的脸上荡漾;当老师讲到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时,用彩笔在黑板上迅速勾勒出雨来的头像,稚嫩的脸庞透露出顽皮的表情,还有几分刚毅,临了不忘甩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惊人之语,重重地敲打在我们的心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上学的路,并不容易。记得学校的门前有一条小河,枯水季节,在河床上搭几块石头,就可以跳跃着过河,一旦下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过河就得蹚水。河水冰冷不说,还会有被水冲走的危险。每当这时,年轻力壮的男老师,都自告奋勇地来到河边。他们或在河的两岸拉一根绳子,让个头大一点的学生拉着绳子过河,或卷起裤管,把个头小的学生一个个从此岸背向彼岸。我那时个头小,不知多少次享受过被老师背过的待遇。老师背着学生在河水中边走边探索的紧张和吃力,还有偶尔跌倒后用身体紧紧护住学生的情形,就像电影画面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缺吃少穿,条件艰苦,山里的孩子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标准极低,常常是一碗苞米饭、就着几根咸菜,就算是一顿饭了,然而对知识的渴望却十分强烈。在熟读了课本之后,便千方百计寻找课外书来读。家里有小人书的,都自发地带到学校来,让同学们分享。
老师们洞悉学生课外阅读的欲望,前后想了许多办法来满足大家的阅读需求。比如,将自己的藏书捐出来,在教室里设置 “图书角”,供学生借阅;与新华书店联系,让他们来学校售书;组织学生开展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得一点劳务费,用于班级添置新书……
一次,学校的丁老师得到一个信息,区里的供销社要收购苎麻。苎麻是一种草本植物,收割后可以提取麻秆表皮上的纤维作为制作麻绳的原材料。丁老师早些年干过这个活儿,对苎麻的种植、收割、粗加工有经验。于是,他便托人从外地买来种子,组织学生在学校前面开荒种麻。几个月后,麻秆长到一人多高,便将其收割下来,置放在事先挖好的土坑里注水压实,进入沤麻阶段。大约一个月后,麻秆沤好了,丁老师就带着学生将麻秆捞上来,把表皮剥下来,经过晾晒,就成为合格的粗加工产品了,再拿到供销社去换钱。这次种麻除去成本共收入80多元。丁老师用这些钱为全班每个同学购买了一本新华字典,还为班级添置了一批新书。后来,虽然有了许多版本的工具书,但这本新华字典,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它,因为它是我用汗水换来的,同时也凝结着老师关爱学生成长的心血。
“在漆黑的夜空点燃自己,为远方的你送去一丝光明……”夜深了,重读泰戈尔的《萤火虫》一诗,便想起为我们送来光明的老师。读书那会儿,家乡还不通电,晚上只能靠煤油灯照明。有些住校学生没有煤油灯,晚自习时只能用从山上采来的松油疙瘩照明。见此情形,老师们便把自己宿舍的煤油灯拿到教室里,还把灯芯特意挑得亮一些,并叮嘱学生要保护视力。煤油灯的光线烘托着寂静的夜晚,微弱的灯光陪伴着学生们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灯下的我们,既得到知识的浸润,也得到爱的滋养。如今,煤油灯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学生时代老师的那盏煤油灯,却一直在我们心中闪亮着,温暖着我们的心,照亮我们前行的路……